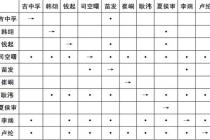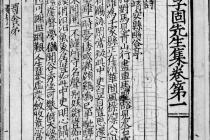从吴姓侨姓关系解读魏晋南北文化的差异与隔阂
中国是一个地域广阔、民族众多的国家。历史上的战争和迁徙经常会造成民族内部或之间的冲突。这些冲突常常不能因为其中某一方的胜利或失败而告结束。冲突裂痕不仅会对人们的社会心理产生难以治愈的创伤,而且在较长时期内对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都要产生深刻的影响和制约。其中世族文人的生活言行是这些影响和制约的显示器。从这个意义上说,通过《世说新语》中魏晋名士的生活言行来观察三国以来分裂局面对当时南方北方文化的差异和融合所产生的影响和渗透,并从中认识和把握当时社会文化的某些深层底蕴,不啻饶有兴味而又意义重大。
“归命侯”不认命
司马氏代魏以后的西晋王朝,看起来已经结束了三国鼎立的分裂局面。在三国旧属的关系中,魏与蜀的最高统治者所代表的社会阶层利益和所奉行的法制基本相同,所以灭蜀后两地之间的政治隔阂很不明显;而吴与魏的统治集团所代表的利益和实行政策却大抵不同(参见陈寅恪《述东晋王导之功业》)。因而灭吴后不仅二者的对立情绪没有消除,反而有增无减。对于西晋王朝的统治者来说,吴蜀两国虽然都已经俯首称臣,但相比之下,“蜀人服化,無携贰之心;而吴人趦睢,屡作妖寇”(《晋书·华谭传》)。西晋统治者在政策措施上尚能明白如何处理与吴人的关系,他们一方面严格控制南人在朝廷的任职,另一方面,他们也注意对江南大族的笼络。当晋武帝问华谭吴亡后的对吴政策时,他建议“当先筹其人士,使云翔阊阖,进其贤才,待以异礼”(《晋书·华谭传》)。毗陵内史在论江南贡举事时也认为江南刚刚归附,贡举方面还应尊重以往的惯例,说明他们主观上还是愿意搞好关系的,但在人们的潜意识中,还难以除去往日的对峙情绪。特别是北方的统治者和世家大族总以胜利者自居,居高临下,俯视吴人。而东吴人本来就不服气自己的失败,加上北人的狂傲,更让人无法忍受。三国以来,中原人把吴人骂作“貉子”,先是关羽把孙权骂作“貉子”(《三国志·蜀·关羽传》裴注引《典略》),接着西晋时孙秀降晋后,晋武帝为了笼络他,便把自己的姨妹蒯氏嫁给了他。但这位蒯氏却十分鄙视自己的丈夫,更不能领会表兄在自己婚姻问题上的政治用意。所以就无所顾忌地骂丈夫为“貉子”。如果不是司马炎的极力回旋,这一句詈语险些使晋武帝计策失算(《世说新语·惑溺》)。苻坚也称寻阳周虓为“貉子”(见刘敬叔《异苑》卷十)。而孟超作为小小都督,统领万人,竟敢公然斥骂作为河北大都督全军统帅的陆机为“貉奴”(《晋书·陆机传》)。在中原大族看来,江东人犹如狐貉一类。有了这种偏见,南北隔阂怎能不日益加深?
当吴国的末代皇帝被带到洛阳,封为归命侯后。一天,孙皓正在借酒消愁时,晋武帝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阴阳怪气地说:“听说江南人好作《尔汝歌》,你能来一首吗?”这个戏弄、侮辱的玩笑说明,在司马炎的眼里,孙皓既不是往日的吴君,也不是今日的归命侯,而是自己的俘虏和阶下囚。而这位归命侯却并不是那乐不思蜀的阿斗,听了司马炎的侮辱之辞,他应声答道:“昔与汝为邻,今与汝为臣。上汝一杯酒,令汝寿万春。”(《世说新语·排调》)在这首《尔汝歌》中,那种沮丧无奈且深恶痛绝的抵触情绪,见诸字里行间。所以尽管吴人名义上已经是晋室的臣民,但很多人怀有家国之恨,拒绝与晋室来往,诸葛靓就是其中一个。
诸葛靓的父亲诸葛诞,被晋文王司马昭所杀,所以诸葛靓对晋室怀有刻骨仇恨。入晋后他被授以大司马的官职,却拒不应召。而且因为杀父之仇,经常背向洛水而坐。小时候,他曾与晋武帝有过交往。晋武帝很想利用这点老交情来笼络诸葛靓,可是诸葛靓的态度又使司马炎很难接近。凑巧诸葛靓的姐姐是司马炎的叔母,于是就请诸葛妃喊来弟弟,司马炎跑到叔母那里去见诸葛靓。见面后,司马炎在宴席上亲热地说:“还记得我们当年的青梅竹马的感情吗?”诸葛靓却说:“只恨我不能象豫让那样,吞炭漆身,为父报仇!” 原来,战国时晋知伯为赵襄子所杀,其门客豫让漆身为厉,吞炭为哑,使自己形貌模糊,欲为知伯报仇(见《史记·刺客列传》)。听了这话,晋武帝只好灰溜溜地离去了(见《世说新语·方正》)。诸葛靓的复仇意识,恐怕不能仅仅理解为孝的表现;而是含有相当的忠义成分,即吴人对北人的仇视心理。
羊酪“PK”莼羹
这种胜利者的狂傲之气不仅表现在晋武帝身上,其他中原贵族,也每每以此亵渎吴人。当吴亡后,中原大族王浑来到建邺,在酒酣之后,趾高气扬地对吴人说:“值此亡国之际,诸位没有什么遗憾的吧?”这股得意忘形而又盛气凌人的狂态,足以令吴人咬牙切齿,不堪忍受。周处答道:“汉末大乱以来,三国鼎立的局面也很快结束了,亡国的不仅是吴人,魏不也被晋所取代了吗?所以怀有亡国之憾的,又岂止我们吴人?”于是王浑羞愧难当(见《晋书·周处传》)。周处这几句软中带硬的回敬,也表明吴人国虽亡,而志不辱,分毫不让的对立情绪。
吴亡以后的最初几年,江南大族顾虑重重,不肯入洛,主要原因就是不肯领教中原人的白眼。陆机、陆云兄弟二人在吴亡后退居旧里几近十年,闭门勤学,太康末始入洛阳。“初入洛,不推中国人士”。陆机入洛后,也自称“蕞尔小臣,邈彼荒遐”(陆机《皇太子宴玄圃宣猷堂有令赋诗》)。陆云《答张士然一首》也有“感念桑梓域,仿佛眼中人”的句子,可见其自卑情绪和桑梓之感。
当少数吴人接受亡国的事实,被迫入洛,对他们来说,是被逼向一个不可知的未来。而到了洛阳以后,他们敏感的神经,总是能清楚地感觉到中原人在言行中处处表现出来的优越感,从而感到无比的屈辱和难堪,所以也毫不客气地予以反击。
当蔡洪来到洛阳,很快就有洛阳人问他:“新政权刚刚设立,众位公卿奉命延揽人才,要从卑微低贱者中寻求才能出众者,从隐居山林者中选取才德贤明之士。先生是南方的亡国遗民,有什么特异的才能来这里参加人才竞争呢?”蔡洪毫不客气地回答说:“夜光珠不一定都出于孟津附近的黄河中,巴掌大的璧玉不一定都从昆仑山开采出来。大禹就出生于东夷,周文王则是出生于西羌。圣贤的出生地未必有固定的处所!当初武王伐纣的时候,把殷商的顽民迁徙到洛阳,各位莫非就是这些顽民的后代?”
这个故事出自《世说新语·言语》,又见载于《晋书·华谭传》和《太平御览》卷四六引《文士传》,均作华谭事。故刘孝标注称《世说》为穿凿。其实这正可以理解为在中原人每每可见的无礼面前,吴人当中流行的反击措辞,以塞洛中人士之口。而把洛人骂为殷之顽民,并非蔡洪、华谭所创,正是当时比较流行的谚语。据《洛阳伽蓝记》,洛阳城东北有上高里,为殷之顽民所居处。高祖名闻义里。迁京之始朝士住其中,迭相讥刺,意皆去之。北魏时成淹和王肃在朝歌也以殷顽民的典故相互戏笑(见《魏书·成淹传》)。这说明从西晋到北朝,殷迁顽于洛邑之事一度流传不衰。可见吴人虽然到了洛中,但南人北人间仍有很多这样能够反映双方对立情绪的口角。陆机入洛后,前去拜访王济,王济在陆机面前摆了几斛羊酪,挑衅地对陆机说:“你们江东什么东西可以敌此?”陆机回答说:“有千里莼羹,但未下盐豉耳!”(《世说新语·言语》)本来,羊酪和莼羹是能够代表南北饮食文化的产品,但这里已经被用来作为双方政治对立情绪的表现工具。王济的狂傲,自与王浑等人不差,而陆机的话中,既有江东人的荣誉感,又饱含对中原人目中无人的极度不满。陆机出身江南大族,又文名显溢,尚得此礼遇,他人便可想而知。
“吴牛喘月”的惶恐
当然,任何时候骨气与气节都需要有奴才作为补充,才能在依存和对比中相互映衬。吴人中也并非没有以失败者自居、诫惶诚恐、唯唯诺诺的奴才。如满奋很怕见风,当他在晋武帝前就坐时,对着窗户直皱眉头。原来北方的窗用琉璃为屏,因为透明,看起来很疏,像透风似的,但实际上很密。当遭到嘲笑并得知风不会吹到自己时,满奋便奴额卑膝地说:“我就象吴牛一样,见月而喘。”因为南方天热,当地水牛怕热,见到月亮便以为太阳又出来,要受酷热了,所以见月而喘(《世说新语·言语》)。这种比喻例是生动形象而又准确传神的。
从蔡洪、陆机二人的际遇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中原人鄙夷江南人的情绪。而满奋以“吴牛”自喻,“见月而喘”,则以江东人自己“见月疑是日”这一贻笑大方的举动,证明中原人对吴人保守、落后、愚昧、无知看法的正确。在这种心理状态下,当孙吴覆亡后,去洛中的南士中,虽然不乏蔡洪、陆机之类旧家大族子弟,但中原人对他们乃另眼看待。有时虽也会得到少数人的赞誉尊敬,如陆机、陆云兄弟来到洛阳后,张华就像见到老朋友一样连称西晋征服东吴的最大收获就是得到了陆氏兄弟(见《晋书·陆机传》)。但像张华那样不以南北为界的宽阔胸襟者,毕竟有限。多半是象王济(武子)那样不加掩饰的无礼。比如陆机刚入洛时,因得到张华的赏识,便向他请教该拜访哪些人,其中提到清谈大师刘惔。陆机到了刘惔家,刘惔正在守哀。一番寒暄之后,刘惔沉默无语,只问了一句:“听说东吴有一种长柄葫芦,您带来它的种子了吗?”陆机兄弟非常失望,后悔来这儿受此羞辱(见《世说新语·简傲》)。
像陆机这样的江南大族子弟,在凭借家族地位和个人努力,登上高位之后,不仅没有得到中原人的信任和尊敬,反而招来更强烈的忌恨,终于与两个儿子和两个弟弟,同时无罪被害(见《晋书·陆机传》)。可见西晋时期虽然南北实行了统一,但二者的对立情绪仍十分紧张,并见诸表面。
“风景不殊,山河有异”
永嘉之乱后,过江的中原土族被称为“侨姓”,东吴的旧姓,则被称为“吴姓”。此后南北对立情绪主要表现为吴姓和侨姓的对立。对侨姓来说,为了民族和家族的生存,要被迫来到这块自己的战败者的土地。于是,昔日战胜者的自豪与今日丧失故土的难堪,以及恐南人不容自己的担心等,相互融合,使他们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而吴姓对侨姓则既有恐惧、戒备,也有鄙夷、敌视以至幸灾乐祸的态度。而二者的对立情绪,由于王导等人的努力,已经由表面化开始向潜在的方面转化。
包括琅邪王在内的侨姓大族,本来对过江就十分勉强,所以在行为上表现出极大的不适。如卫玠在准备渡江的时候,“形神惨悴,语左右云:‘见此芒芒,不觉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复谁能遣此!”(见《世说新语·言语》)这种对过江极不情愿的心情,固然有不忍故国流落他人之手的因素,但如联系长期以来南北的对立情绪,就不能排除后者所带来的顾虑。从吴亡归晋到永嘉后琅邪王过江,已经三十多年,可是当司马睿过江以后,竟对吴人顾荣说:“寄人国土,心常怀惭。”(《世说新语·言语》)说明南北隔阂之深远。元帝的“怀惭”,也许既有对昔日中原人过分狂妄的忏悔,也有对长期以来双方关系合睦缺乏远见的反省。不仅晋元帝如此,当时的过江大族每至暇日,经常在新亭借酒浇愁。一次,周顗望着江南的山河说:“这里的风景与北方也没什么两样,但却有山河之异的感觉。” (《世说新语·言语》)其实,南北的风景倒是相差很大,周顗真正慨叹的潜台词是,即使这里的风景与北方完全一样,也觉着这不是自己的家乡。可见南人固然不附,不以北人为同胞,北人也同样不以吴土为国土。虽被迫迁此,终有寄人篱下之感。周顗的话,说明北人已明白表示不愿立足江东。而晋室要苟延残喘,又必须借寓江东,积蓄力量,以求一逞,这样就必须解决吴姓侨姓的关系问题。
平心而论,当琅邪王带着部属来到南方时,其安定局面的建立,困难的确很大。由于陆机兄弟子侄的被害,由于三吴旧家大族近年的际遇,以及数年来南北人们心灵上的抵牾,要在南人痛恨北人的巅峰时代与之相安,确非易事。然而,在王导“以吴制吴”和宽纵大族怀柔政策指导下,琅邪王终于解决了吴姓侨姓间的团结问题,至少是表面的团结。吴姓政治待遇和地位的改变,对二姓间的心理机制產生了复杂而又微妙的影响。对吴姓来说,王导辅政后,的确使他们在各方面得到一些既得利益,再像从前那样跟中原人对着干,于道义、于自己的生存都不利;对侨姓来说,这种让步是不得已的,是为了在南方立足,以求复国之机。为此,才不得不尽可能表现出对吴姓一视同仁的态度。应当承认,这种表面上对立情绪的缓和,对稳定东晋局势,起了重要的作用,但不能因此就认为二姓间的对立情绪已经荡然无存。因为心灵的鸿沟并不像有形的裂痕那样容易弥合,而且即使弥合了,印记总还是存在的。王导辅政二姓间的对立和隔阂,在表面上是少多了,但仍存在。如王导过江后为了笼络吴中大族,向陆玩提出联姻,遭到严厉拒绝。王导的请婚,显然是出于政治用意,而绝未料到如此狼狈。陆玩作为王导的下属而态度如此决绝,说明在他的意识中,吴姓与侨姓通婚,竟无异于乱伦。一次陆玩去拜访王导,王导招待陆玩的食品即是当年王济款待陆机的北方特产——羊酪。陆玩回家后,当天就病倒了。第二天,他写信给王导说:“昨天晚上吃羊酪多了一点儿,难受了一夜。我虽然是吴人,却差点儿成了中原之鬼。”(见《世说新语·排调》)从中也可见出二姓问难以弥合的裂痕。
不过,这样公开表面化的对立在东晋时已比较少见,较多的还是潜意识中以不自觉方式流露出来的隔阂。如许璪和顾和都是吴姓,二人都在王导手下任丞相从事。表面看起来,他们已经成为东晋统治集团的成员,可以和其他侨姓官员一样,游宴集聚,略无不同。有一次在王导那里玩到半夜,仍兴致勃勃。王导见天色已晚,便让二人在自己的帐中睡觉。许璪上床便鼾声大作,而顾和却辗转反侧,久不能寐。王导心里很得意,嘴上却言外有意地说:“这儿已经没有我睡觉的地方了。”(见《世说新语·雅量》)表面看来,这是何等的融洽、和睦。可是顾和的辗转反侧,却使人感受到这位吴姓官员在受宠若惊之后的一种局促和忐忑——这恰恰是侨姓官员所不会具有的。而王导的专招吴姓官员入己帐中和向众人表白无处睡觉,也明显具有做秀的痕迹——对侨姓官员是用不着这样的。又有一次,吴姓的谢奉被罢免吏部尚书还乡,侨姓大族谢安应公外出,与谢奉路遇,就故意停留三天,想多劝慰几句。不想谢奉每次都以别的话题岔开,竟没有机会言及罢官之事。谢安深以为憾,对同行者说:“谢奉故是奇士!”(见《世说新语·雅量》)其实,造成谢奉冷淡的原因,并不是奇不奇士的问题,而是二姓的隔阂问题,致使侨姓的谢安存心而无法相通。这种隔阂,在二姓内部,是没有的。如有度量而无才学的魏长齐初次外出做官时,虞存嘲笑他说:“和你约法三章:谈论的人处死,写诗文的人判刑,品评人物的人治罪。”魏长齐高兴地笑着,没有一丝抵触的神色(见《世说新语·排调》)。只有在自己人中间,才能这样毫无顾忌地大开玩笑,而对方也毫不在意。如在二姓之间,这样的嘲戏无疑将是一场纠纷的导火索。因为为了顾全大局,大家可以不计宿怨,通力合作。可是在许多日常生活琐事上,由于潜在的南北隔阂在起作用,经常会出现一些虽无关大局而又明显龃龉的场面。有趣的是,这些故事中有的只能由双方在心灵上互相感应,只能意会,却无法端到桌面上来。如王导虽然十分重视团结吴姓,但也有疏忽的时候。一次顾和去看他,正值王导倦乏,竟然当着客人的面睡着了。顾和却非常担心,对同坐说:“听说元帝在江东的局面全靠王丞相协助。可他身体如此,令人担心。”(见《世说新语·言语》)王导忽略了自己的病态形象可能产生的副作用。而顾和那不冷不热的话中,也使人体味出一丝淡淡的揶揄。还有一次,当江东人到王衍那里咨询问题时,也赶上王衍疲劳,则干脆打发他们到裴頠那里去了(见《世说新语·文学》)。说明像王导、王衍这样的大政治家,虽然深明二姓团结大义,但潜意识中的隔阂,仍不自觉地流露出来。
不过从趋势上看,吴姓和侨姓还是逐渐地走向相安和合睦。如吴姓张玄和桥姓王忱本不相识,后来在王沈的舅舅范宁那里相遇了。范宁让他们二人交谈,目的是使二姓能相安平和。可是两个人都不肯先放下架子,一个正襟危坐,一个盯着客人沉默不语。张玄很失望,就起身而去。范宁苦苦相留,也沒留住。范宁就责备外甥说:“张玄是吴士之秀,而且见遇于时,你这样对待他,真让人不能理解!”王忱笑着说:“如果张玄想与我相识,就应专程来拜访。”范宁立即通知张玄,张玄便整装来访,“遂举觞对语,宾主无愧色”(《世说新语·方正》)。与前面数事相比,这个故事在侨姓自大、吴姓自卑这一基本点上是相同的。但不同的是,这里已经有了愿为二姓团结苦心周旋的范宁。而且双方都有着愿意,至少是不反对合睦交往的愿望。这对于二姓的合睦,又是至关重要的条件。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
本站所有文章、数据、图片均来自互联网,一切版权均归源网站或源作者所有。
如果侵犯了你的权益请来信告知我们删除。邮箱:dacesmiling@qq.com
宁稼雨 已更新 18 篇文章
- 《古典文学知识》2022年1期解读魏晋名士服药(下):服药活动的精神和社会功效
- 《古典文学知识》2021年6期解读魏晋名士服药(上):寒食散及其实际功用
- 《古典文学知识》2021年5期解读魏晋名士饮酒(4):从兴亡之兆到慢形之具
- 《古典文学知识》2021年4期解读魏晋名士饮酒(三):从治病养生到及时行乐
- 《古典文学知识》2021年3期解读魏晋名士饮酒(二):从礼制的附庸到礼教的叛逆
- 《古典文学知识》2021年1期解读魏晋名士饮酒(一):从崇拜神灵到个体逍遥
- 《古典文学知识》2020年6期魏晋人物品藻活动从实用到审美的评价转变
- 《古典文学知识》2020年5期汉代以来人物品藻风气的影响与盛行
- 《古典文学知识》2020年4期魏晋时期江南一带对中原文化其他方面的趋从与跟进
- 《古典文学知识》2020年3期魏晋时期南北政治格局变迁对学术文化的影响
分类排行
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