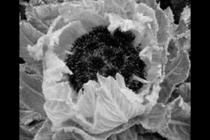建安二十二年的瘟疫与魏晋文学批评的确立
中国古代很早就有关于瘟疫的记载,当时文献多称之“疫”“疠”,或是合称“疫疠”。若论瘟疫发生频率之高、程度之烈,或以东汉为最。据《后汉书》《三国志》的记载,东汉自光武帝建武元年(25)至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220),196年间共有26个疫灾年份,而汉献帝在位31年里竟然就有7年发生疫情。瘟疫的频发与漫延,不仅会造成百姓流离、人口锐减,还会对当时的军事、政治等产生重大影响。而爆发于建安二十二年(217)的这场瘟疫,还对当时文坛产生了重要影响,推动了魏晋文学批评的确立。
有关建安二十二年的这场瘟疫,史书不乏记载。范晔在《后汉书·五行志》中记云:“献帝建安二十二年,大疫。”惜字如金的史官虽然只说了一句话,但将此疫单独列出,并冠之以“大”,已令人隐然感觉到疫情之严重。《三国志》的记载要比《后汉书》详细许多。据《三国志·魏书·司马朗传》,建安二十二年曹操遣夏侯惇、臧霸南下征吴,行至居巢(今属安徽省巢湖市),“军士大疫”。曹操当年鏖战赤壁时领教过瘟疫对军队的杀伤力,故急命“(司马) 朗躬巡视,致医药”。然而疫情之猛烈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派去的丞相主簿司马朗竟也“遇疾卒”,时年 47 岁。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当时随军出征,也染疫身亡,时年41岁。瘟疫没有就此停住,而是随着军队流动扩散开来,很快蔓延至曹魏都城——邺城。曹植在《说疫气》一文里曾有描述:“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人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耳。若夫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门,若是者鲜矣。此乃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曹植一方面描述了当时疫情之惨烈,竟有“阖门而殪”“覆族而丧”的惨况;同时指出了被褐茹藿、荆室蓬户的平民的感染率要远大于上层贵族。这应该跟卫生条件、防疫措施、饮食营养等都有关系。然而曹植忽略了底层平民与上层贵族之间的中间阶层,即文人阶层,他们中的很多人都被这场瘟疫夺去了生命。例如曾在曹操手下任司空军师祭酒的陈琳、五官将文学的徐幹、丞相掾属的刘桢和应玚,皆殁于此疫。加上死于军中的王粲,建安七子中竟有五子死于这场瘟疫。事后曹丕每念及于此,便不胜伤悲,如其在《又与吴质书》中所言:“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
我们知道,建安文学的彬彬之盛是由三曹和七子共同开创的,但七子中的孔融已于建安十三年被杀,阮瑀于建安十七年去世,现在一场瘟疫又夺走剩余五子的生命,建安七子至此无一存世。如果将七子视为邺下文人集团的中坚力量,那么可以说建安二十二年的瘟疫致使邺下文人集团遭受了灭顶之灾。文坛宿将只剩下三曹,曹操又已暮年,即将于三年后(建安二十五年)去世,真正的作手只有曹氏兄弟了。尽管曹丕“天资文藻,下笔成章”(《三国志·文帝纪》),曹植更是文才富艳、才高八斗,但两个人无法撑起一个时代的繁荣。从俊才云蒸到文坛凋零,这是这场瘟疫给建安文学的一大打击。除此以外,建安文学的主题与风格也受到影响,发生着转变。建安前期,由于曹操的东征西讨和邺下文人的聚集,诗歌以关注现实与游宴酬赠为主题。前者如王粲的《七哀诗》、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等,慷慨多气之中可见执着奋进之心;后者如曹植等人的《公宴诗》、刘祯等人的《大暑赋》等,多是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的作品,以高谈娱心、欢畅纵情为特征。可是建安二十二年的这场大瘟疫使许多文人才士皆登了鬼录,一时间,当年的奋进都化为了乌有,昔日的欢宴也成为了记忆。幸存者只能发出“人生居天壤间,忽如飞鸟栖枯枝”(曹丕《大墙上蒿行》)、“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晞”(曹植《赠白马王彪》其五)这样的哀吟,来感叹生命的无常与人生的无奈。慷慨雄健、风骨遒劲的建安诗风与“酒酣耳热,仰而赋诗”的邺下诗会,都在这一年徐徐落下了帷幕。
这场瘟疫对建安文坛还有一大影响,往往为人忽略,那就是推动了魏晋文学批评的确立。建安文士不仅开展了大量的文学写作,还热衷于相互评论。七子间互有评论,但互评不是太高,曹丕谓之“文人相轻”;曹丕、曹植对他们也有评论,相对客观;吴质、刘季绪等人也热衷于评点文章——这些已经构成一种自觉的文学批评现象。其中曹丕的《典论·论文》,提出了文学价值论、文气论、文体论等命题,无论是理论性还是系统性,都可视为魏晋文学批评得以确立的标志。
据《三国志·文帝纪》注引《魏书》,曹丕为太子时“疫疠大起,时人凋伤”,他就写信给王朗,抒发哀情,同时“故论撰所著《典论》、诗赋,盖百余篇,集诸儒于肃城门内,讲论大义,侃侃无倦”。曹丕给王朗的信,署建安二十二年冬,可知《典论》的主体部分包括《论文》在内,应作于是年。曹丕为何会在这一年撰写《典论·论文》呢?我们可以笼统地说建安文学批评是文学创作高度发达的结果,也是鄴下文人交流经验、谈艺论文的产物。这些都是《典论·论文》得以出现的必要条件。但是事物的产生往往还有一个直接推动因素,这个因素导致曹丕在建安二十二年而非二十一年或二十三年来撰写《典论·论文》。从信中“疫疠大起,时人凋伤,余独何人,能全其寿”的感叹来看,这场夺走五子生命的大瘟疫给曹丕造成了很大的震动,对生命价值的思考促使他写下了这篇不朽的文字。
曹丕常在邺城与徐幹、陈琳、应玚、刘桢等人诗酒谈艺,他在建安二十三年写给吴质的信中回忆往日与诸子的交游:“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谓百年已分,可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又与吴质书》)曹丕是一位情感敏锐细腻的诗人,言语间流露着与徐、陈、应、刘等人的深厚感情。面对逝者,他想用某种方式来作纪念。在道教盛行的汉代,死后飞升、游于仙界,是人们着力追求的一种不朽的方式。但是瘟疫中生命的脆弱,很大程度上消解了曹丕对神仙的迷信,他看到很多人为追求成仙成道而丧命,不由感慨“古今愚谬,岂唯一人哉”(《典论·论方术》)。曹植也说那些方士是“挟奸宄以欺众,行妖隐以惑民”,至于神仙传说,“自家王与太子及余兄弟,咸以为调笑,不信之矣”(《辩道论》)。所以曹丕没有写游仙诗来纪念邺下诸子。
既然神仙不可信,那如何才能彰显邺下诸子的生命价值呢?曹丕准备给他们编文集,“撰其遗文,都为一集”(《又与吴质书》)。显然这是受传统“三不朽”思想的影响。《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载,穆叔去晋国,范宣子来问他,什么是古人所谓的“死而不朽”?穆叔提出了“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的说法。曹丕在《与王朗书》中说过类似的一段话:“生有七尺之形,死惟一棺之土,惟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文人,与立功无缘,也不以修德见长。曹丕曾对吴质说:“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与吴质书》)所以文人想要不朽,“立言”是最好的方式。曹丕为他们编纂文集,就是出于这个目的。但是古人所谓立言不朽之“言”,主要是指关乎教化与训勉的言论,并非文学意义上的文章。曹丕就凭借自己的身份与地位,将文章抬升到“立言”的高度,使其同样具有不朽之价值。这样,他就能在《典论·论文》中高呼:“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也就是说,徐、陈、应、刘等人不必依托显赫的政治地位,也不必凭借史家之笔,只要有锦绣文章传世,就可以获得不朽的价值。从此,历代文士都可以像邺下诸子一样,依靠文字来抵抗死神,凭借文章来传世不朽。所以《典论·论文》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不仅吹响了文学自觉的号角,而且以对各家创作得失的分析和对文体的划分,奠定了魏晋时期文学批评的基础。可以看出,这场大瘟疫对生命的侵噬和对幸存者造成的创伤,是曹丕写作《典论·论文》的直接诱因。
考虑到建安二十二年曹丕被立为魏太子,《典论·论文》的写作不排除含有安慰政治对手曹植,消弭其抵抗情绪的用心。但从对邺下诸子创作特点的分析与品评来看,曹丕的主要目的还是在于通过纪念逝者来总结自己对文章写作、文体特征的一些看法。当然,曹丕撰写《论文》归根到底是基于汉末建安时期文学创作的繁荣与评论活动的活跃,但当必要条件都具备的时候,往往是一个偶然因素来直接推动事物的产生与发展。像瘟疫这样的自然灾害不仅会给人们造成肉体和心灵的创伤,也会在无意间推动一些事物的产生,或是改变其发展的方向。当我们审视文学史进程时,不可忽视这种看似偶然的因素所起到的历史作用。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文学院)
本站所有文章、数据、图片均来自互联网,一切版权均归源网站或源作者所有。
如果侵犯了你的权益请来信告知我们删除。邮箱:dacesmiling@qq.com
曹明升 已更新 2 篇文章
- 《古典文学知识》2020年5期建安二十二年的瘟疫与魏晋文学批评的确立
- 《古典文学知识》2019年2期项鸿祚三题
分类排行
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