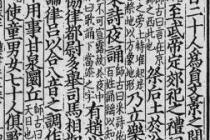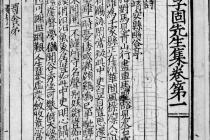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疏证(三)
汉家之厄今十世,不见中兴伤老至。
一死从容殉大伦,千秋怅望悲遗志。
从汉朝写起,亦是循静安思路。吴宓与蒋天枢两家注(以下称“吴注”“蒋注”)均提及宋汪藻《浮溪集》所载其代隆祐后孟氏所撰高宗即位诏有“汉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兴;献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之句,两家注均认为是以汉朝经历十世而遭遇厄运比喻清朝自顺治至宣统十朝,同样面临着内忧外困的情况。诗句出自《浮溪集》,应是陈寅恪指明文献线索,估计陈寅恪也不遑多说,但两家注似未深究陈寅恪之意,汉家十世而厄,幸得光武帝刘秀出,力平王莽篡政,令汉朝得以中兴。故其小序中也有“若以君臣之纲言之,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之句,乃以刘秀为君王之杰出者。而宣统帝如此年幼,事实上后来也无汉光武帝刘秀之雄才大略,故清朝“不见中兴”。
谁不见中兴?虽是泛泛而说,其实是指向王国维,故吴注云王国维“祈望宣统帝能复兴清朝”,只是年至五十遂绝望复兴之事,故从容自沉,以“殉大伦”。小序只说纲纪,而未及五伦八德之事,所谓“五伦”是指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五种关系,即君臣有义、父子有亲、长幼有序、夫妇有别、朋友有信;“八德”是指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者。“纲纪”与“五伦”有交叉重合也有区别。“五伦”以“君臣有义”为首,亦称“大伦”,故“殉大伦”,意即王國维乃是殉清室而死,此诗句明白说出者。对勘小序,纲纪虽也有“君为臣纲”之说,只是就君与臣两者之行政关系而言的,而作为“五伦”的“君臣有义”则是从道德情感方面而言。虽然道德关系受制于行政关系,两者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但毕竟论说角度还是有差别的。我因此怀疑陈寅恪是先有诗,后有序。诗歌要铺写王国维一生之经历,而小序则擢拔乎上,抽象言说其自沉原因,故意思稍有偏离,也是正常的。换言之,陈寅恪在诗歌中说王国维乃殉清而亡,指向分明,而在小序中则又将王国维之死的原因超乎一朝一姓之上,其后来的补证似乎也表达着对诗歌本身部分的否定之意。所以小序与诗歌并非彼此契合无间,而是稍有旁逸甚至矛盾的。诸家多以挽词与序为珠联璧合,笔者实蒙所未解。
蒋注未注“一死”二句,吴注则较详细,吴宓认为“殉大伦”不能从一般意义上去理解是以臣之生命殉君王,此意必须是君王驾崩,才能真正合乎“殉大伦”之义,故吴宓说:“宣统尚未死,王先生所殉者,君臣(王先生自己对清朝)之关系耳。”这个解释有点勉强,若说君臣关系,则始终存在,但何以在某年某月某日自沉,自然是有直接的诱因的,至少在选择自沉时间上,是一个值得考量的问题。这种模糊的说法其实难以引向对王国维自沉原因的实证考察。所以陈寅恪的诗、吴宓的注,我觉得至少在这里应该是有问题的。陈寅恪的小序似在调整其看法,而吴宓的注则为诗歌所牢笼了。
“千秋”一句,蒋无注。吴注云:“杜甫《咏怀古迹》诗宋玉一首:‘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后世之人哀悼王先生,而悲王先生之忠节(其望清复兴之志)。”吴宓的注释显然要继续呼应前说,故将静安之遗志指实为“望清复兴之志”。但前已述其立说勉强之意,此亦不过继续勉强而已。但平心而论,陈寅恪的诗歌既前说“殉大伦”,又继说“悲遗志”,吴宓的注释从落实陈寅恪诗意的连贯角度来说,也是可以理解的。吴注引杜诗,或亦为陈寅恪所指引。杜甫曾有《咏怀古迹》五首,其二云:“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江山故宅空文藻,云雨荒台岂梦思。最是楚宫俱泯灭,舟人指点到今疑。”此写杜甫追怀宋玉、凭吊楚宫怅然而生今昔之感。昔宋玉悲秋,实空怀忧国之心,但楚宫仍是泯灭无影。陈寅恪此句也是说王国维曾有深切的忧虑大清危亡之心,但清朝也终究一去不复返矣。故以杜甫追怀宋玉与楚宫来喻指千秋以后的人追思王国维及其王国维对大清王朝曾经的忧虑之心,其间盖有“萧条异代不同时”之感生矣。
从陈寅恪开笔四句来说,其实将王国维之死因基本归于“殉清”,故吴宓之注也紧护其说,刘季伦也将开笔四句作为全诗命意所在,认为点出了观堂对清室、对溥仪的极深感情(参见刘季伦《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诗笺证稿》,《东岳论丛》2014年第5期)。但这四句与小序所言“殉文化”之说颇有差距,小序颇有摆落诗歌、凌空而起之嫌。
曾赋连昌旧苑诗,兴亡哀感动人思。
岂知长庆才人语,竟作灵均息壤词。
此诗句有蒋注,无吴注,鉴于吴注在“文革”中多散失的事实,或吴注原有也未可知。蒋注云:“王先生壬子春在日本时,作长诗《颐和园词》述晚清事,中有句云:‘昆明万寿佳山水,中间宫殿排云起。拂水回廊千步深,冠山杰阁三层峙。后竟自沉排云殿前湖中。”此注契合句意,但稍显跳跃。长庆才人本指元稹、白居易,因他们在唐穆宗长庆年间写作的大量长篇叙事歌行体诗而得名,两家也分别有《元氏长庆集》《白氏长庆集》诗集,陈寅恪诗中应指元稹,因其曾有《连昌宫词》,陈诗中“连昌旧苑诗”即指此。陈寅恪其实是以元稹《连昌宫词》指代王国维《颐和园词》,所以“长庆才人”也就转而指王国维了。王国维的《颐和园词》从咸丰出奔热河写至清亡,将晚清政坛的变化以及最终导致倾覆的过程和原因都勾勒了出来,故其兴亡哀感动人情怀。而所谓“长庆才人语”则并非指《颐和园词》全部,而是其中写及昆明湖及其周边的迷人景色如“昆明万寿佳山水,中间宫殿排云起。拂水回廊千步深,冠山杰阁三层峙”云云,似乎冥冥之中,王国维注定要在这片佳山水中终结自己的生命。“灵均”是屈原的字,“息壤词”出《战国策·秦策》“秦武王与甘茂盟于息壤”之句,后以“息壤”为盟约之意。此句意为王国维自沉昆明湖,对照其《颐和园词》,似乎早就相约似的,宛然诗谶,其精神仿佛屈原自沉汨罗江。时近端午节,王国维又写过《屈子文学之精神》的宏文,而其自沉的方式也与屈原同,故陈寅恪诗将其与屈原沉江联类而谈。实际上将王国维与屈原的自沉并论也是当时普遍的说法,此稍检《王忠悫公哀挽录》,几开卷可见,陈寅恪不过于此再次强调了这一点。
依稀廿载忆光宣,犹是开元全盛年。
海宇承平娱旦暮,京华冠盖萃英贤。
前两句回忆清末光绪、宣统之二十余年,光绪(1875—1908),宣统(1909—1911),若合乎完整的光绪、宣统之年应有三十六年之久,何以只说“依稀廿载”?检诸家笺注,似皆未得其实,其实陈寅恪应是从其出生之1890年为起始,至1911年辛亥革命而止,前后21年,故取其成数言“依稀廿载”,强调亲身经历而已。且其所拟的唐代开元年间,也不足三十年。而尤为诸家所不解的是清末国势危殆,陈寅恪何以拟之如唐之鼎盛之开元年间(713—741)?此句当然由杜甫《忆昔》“忆昔开元全盛日”化出。但杜甫乃是在安史之乱后追怀开元承平之治,而陈寅恪则是居民国而忆清末,在陈寅恪看来,清末固然有衰颓之势,然相较民国之纷乱,犹有胜处。只是陈寅恪出语稍重,以至于令后人生疑,或以为“令人费解”,或以为“出语太失分寸”,或以为表明其“封建地主阶级的立场”(参见胡文辉《陈寅恪诗笺释》1927年[民国十六年丁卯],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然寅恪先生的语境不可不知,清末虽内忧外患,然封建制度尚在,藉制度以生存的传统文化尚在。在陈寅恪看来,这就是英贤犹在的承平欢娱景象。1964年,陈寅恪在《赠蒋秉南序》中说:“清光绪之季年……朝野尚称苟安,寅恪独怀辛有索靖之忧,果未及十稔,神州沸腾,寰宇纷扰。”(《寒柳堂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所谓“神州沸腾,寰宇纷扰”即指民国建立。陈寅恪还说:“余少喜临川新法之新,而老同涑水迂叟之迂。盖验以人心之厚薄,民生之荣悴,则知五十年来,如车轮之逆转,似有合于所谓退化论之说者。”(陈寅恪《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载《寒柳堂集》)读此二节文字,即知寅恪先生虽然将清末之光宣拟之如唐之开元,其意或稍模糊,而其心志固未尝不明晰也,盖以“人心之厚薄,民生之荣悴”作为标准,注重的是纲纪道德之说从厚到薄、由盛而衰的变化而已。陈寅恪《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一文撰于“乙酉孟夏”,亦即1945年,逆推五十年,也正是光绪之季年。其实陈寅恪在诗、联中使用“开元全盛”之词还有其他的例子(参见吴宓著,吴学昭整理《吴宓日记(1928—1929)》,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8页;《陈寅恪诗笺释》,第66页)。这说明“开元全盛”云云更多的只是表达一种追怀昔日纲纪昌明的情怀而已。
当日英贤谁北斗,南皮太保方迂叟。
忠顺勤劳矢素衷,中西体用资循诱。
光宣之时京华荟萃群贤,其中堪称北斗的则是张之洞。张之洞(1833—1909)乃直隶南皮(今属河北省)人,卒后追赠太保。迂叟乃北宋之司马光之号,据《抱冰室弟子记》所载,张之洞尝自比为司马光。此“南皮太保方迂叟”之大义也。然张之洞何以自比司马光?检《抱冰室弟子记》,张之洞自言生性疏旷,难称外吏,不如为京朝官,以读书著述终其身。其引为前例的便是司马光已官中丞,依旧居洛著书十八年。可见他希望如司马光一般,先读书著述,再出而为官。“忠顺勤劳”本是《晋书·陶侃传》引尚书梅陶评价陶侃“忠顺勤劳似孔明”之语,张之洞亦尝自比陶侃之忠顺勤劳,时人若郑孝胥等亦以陶侃视之。张之洞尝著《劝学篇》,明确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权衡斟酌乎中西之间,既不离经叛道,又能关乎时代,以中学为内学治其身心,以西学为外学应乎世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首倡者虽非张之洞,但张之洞深化并扩大了这一思想,并最终使这一思想成为清末统治阶层的政治共识。张之洞以“忠顺勤劳”之德性与“中西体用”之系统学说,而成为当日英贤之北斗。陈寅恪虽游学美洲、欧洲,但在对待中西文化的关系上却一直与张之洞同调。蒋天枢说:“先生对于历史文化,爱护之若性命。早岁游历欧美各国时,仍潜心旧籍,孜孜不辍,经史多能闇诵。其见闻之广远逾前辈张文襄,顾其论学实与南皮同调。《观堂先生挽词》所谓‘中西体用资循诱者是也。”(蔣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总持学部揽名流,朴学高文一例收。
图籍艺风充馆长,名词瘉野领编修。
清末学部类似今之教育部,设立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初由荣庆主持,此后才由张之洞曾以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身份管理学部事务,并因此吸纳了一批优秀的人才。其中有以朴学(考据学)鸣世者,也有以高文(辞章)称雄者。缪荃孙(号艺风老人)曾任京师图书馆监督,严复(号瘉野)曾主事名词编译馆,“领编修”云云指此。此数句承南皮太保称北斗之意而下,而称扬张之洞的管理才能和格局。张之洞总持学部虽在荣庆之后,但在其主持之下,既有如缪荃孙这样的朴学家出任京师图书馆监督,又有如严复这样的文章高手主事名词编译馆,可谓用人得宜。此亦呼应之前“京华冠盖萃英贤”一句,若缪荃孙、严复皆属英贤之列,而非只是就“学部”论列诸家。罗振玉在接获陈寅恪此诗后复函云:“此篇中间叙图书局,似误混为图书馆,图书局直隶学部,主编译教科书及审定等事,其局长以丞参兼之。至图书馆,庚辛间始开创,馆长为艺风,忠悫未尝任馆事也。”因为罗振玉曾在学部任职,故对学部各职能部门非常了解,而陈寅恪在此用“总持学部揽名流”一句,接言京师图书馆与名词编译馆,确实容易被误解为皆就学部之内言“名流”。然此后并未见陈寅恪有修改之迹,盖罗振玉所言学部与图书局及京师图书馆事固亦合乎事实,然陈寅恪虽重点在说张之洞,但其文脉实是承“京华冠盖萃英贤”而来,乃由张之洞来,而非至张之洞止。
校雠鞮译凭谁助,海宁大隐潜郎署。
入洛才华正妙年,渡江流辈推清誉。
至此言及王国维。1906年初罗振玉为学部尚书荣庆奏调,入为学部参事。王国维随同北上,但未入职。同时在《教育世界》发表《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颇多与张之洞之说对立者。次年春因罗振玉推荐,入学部为编译图书局编译(局员),兼总务司行走,主编译及审定教科书等事,陈寅恪诗中“校雠鞮译”,便主要对应这一职务。1909年,学部设立编定名词馆,严复任总纂,王国维任名词馆协修。此亦呼应前之“名词瘉野领编修”一句。据学部编译图书局局长袁嘉谷回忆,王国维入学部时,张之洞尚在两湖总督任上,两年以后,张之洞得补军机大臣兼管理学部事,故王国维在学部与张之洞发生职务上联系的时间也就是一年左右。据说当时因为国际交流的需要,学部需要撰写国歌,张之洞遂要求学部人员多提供作品,王国维也作了一首,袁嘉谷虽然觉得王国维所作国歌最为畅达,但因歌词太长,担心不易记诵,所以就搁置下来,没有送到张之洞那里去(参见袁嘉谷《我在学部图书局所遇之王静安》,《王国维全集》第二十卷,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袁嘉谷《王静安国维别传》,《云南旅平学会季刊》第二卷第一期[第五号],民国二十四年[1935]四月三十日出版)。可惜这篇长长的国歌现在也不见踪影,若不是袁嘉谷自作主张,张之洞有机会读到王国维的作品,说不定会别具青眼,则王国维这首国歌或许早已名扬四海了。但与严复共事的时间则较长。“校雠鞮译凭谁助”一句正言其协助严复之事。清末学部编译图书局局长袁嘉谷在1928年6月27日的演讲中特别说:“陈君寅恪的诗,仿佛只知有张文襄,是有点不确的。”(《王国维全集》第二十卷)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首刊于1928年4月之《国学论丛》第一卷第三号,袁嘉谷在两个月后的演讲即已提及,可见陈寅恪此诗发表后传播速度之快。“海宁”指王国维,因其籍贯浙江海宁。“郎署”指京曹即司官以下之属官,王国维虽任职学部,但一如隐于朝市之大隐,潜心于分内之事,不事交游,陈寅恪下一“潜”字,足见王国维之静默之心性特征。学部编译图书局局长袁嘉谷对此也印象特深,他回忆说:“静安性情实在特别,当他在我下面做事的时候,自入局之日定一个坐位,每日只见他坐在他的一个坐位上,永不离开。……他为人真是简默,在局三年,不曾说上一百句话,别人与我高谈雄辩,而他静坐不语。”“我想静安这个人正是如庄子所说的‘木鸡一样,他一言不妄发,一事不妄为。”(同上)王国维入京在1906年,时年29岁,一如当年陆机陆云兄弟吴亡后入洛,年亦未至三十,皆在人生妙年。西晋南下灭吴后,诸时流名辈皆深赏“二陆”之才华,而入京后之王国维,虽其生活常态一如朝中隐士,而其才华同样赢得京城士人交相称赏。此四句写王国维入学部后之生活以及备受时流推崇之情形。
闭门人海恣冥搜,董白关王供讨求。
剖别派流施品藻,宋元戏曲有阳秋。
此言其著述《宋元戏曲考》之情形。王国维虽在学部谋生,然业余时间皆花费在搜求宋元戏曲资料上,若董解元、白朴、关汉卿、王实甫等所著曲作因此而成为王国维熟读之物。王国维不仅将宋元戏曲分为文采派、本色派等,同时也对其结构、唱词进行品评,勾勒出宋元戏曲的发展轨迹。王国维此书初拟名《宋元戏曲考》,出版时被改为《宋元戏曲史》。王国维曾对陈寅恪说:戏曲史之名可笑。盖嫌其名不雅,且范围过广不切合内容也。显然王国维认为他写的只是“宋元戏曲考”,对宋元戏曲的若干重要问题进行考论,而非将宋元戏曲的整个面貌和发展轨迹进行研究。看来“宋元戏曲史”之名之产生,是王国维屈服于出版家意见的结果,而出版家则是考虑书名可能的文化影响和社会影响,不暇考虑其范围与内容矣。陈寅恪何以对王国维的戏曲研究特此青睐,即因为王国维关于戏曲的系列研究,不仅有扎实的文献工夫,更有科学的研讨方法。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陈寅恪在讲述欧阳修专题的时候曾说:“今日中国,旧人有学无术,新人有术无学,识见很好而论断错误,即因根据之材料不足。朱子有学有术,宋代高等人物皆能如此。”(卞僧慧纂,卞学洛整理《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附录《陈寅恪先生欧阳修课笔记》,中华书局2010年版)对照陈寅恪的这一对“学”与“术”的分析,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确实是当之无愧的,正因为兼备学与术,所以王国维的戏曲研究不仅开启法门,而且蔚成峰峦,长时期地引导着戏曲研究的方向。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文系)
上一篇:国学研究与清代考据学(下)
下一篇:“一片冰心在玉壶”
本站所有文章、数据、图片均来自互联网,一切版权均归源网站或源作者所有。
如果侵犯了你的权益请来信告知我们删除。邮箱:dacesmiling@qq.com
彭玉平 已更新 7 篇文章
- 《古典文学知识》2022年1期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疏证(七)
- 《古典文学知识》2021年3期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疏证(六)
- 《古典文学知识》2021年2期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疏证(五)
- 《古典文学知识》2021年1期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疏证(四)
- 《古典文学知识》2020年6期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疏证(三)
- 《古典文学知识》2020年5期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疏证(二)
- 《古典文学知识》2020年4期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疏证(一)
分类排行
推荐阅读